罕见老照片:80年代安徽黄山市,以前叫徽州,风光古朴又自然。
你还记得徽州老样子吗,白墙黑瓦贴着青山,河里有竹排,巷子里有吆喝声,这组老照片把我一下子拉回去,名字从徽州变成黄山市了,人情味和山水味却没变。
 图中这一排白墙黑瓦叫徽派民居,粉墙黛瓦马头墙,屋脊像燕尾一样翘起,房子顺着山势一层叠一层,雨季从马头墙缝里往下滴水,院口就能听见潺潺声,我娘说,这样建,冬不冷夏不闷,靠山吃山的道理全在屋檐上了。
图中这一排白墙黑瓦叫徽派民居,粉墙黛瓦马头墙,屋脊像燕尾一样翘起,房子顺着山势一层叠一层,雨季从马头墙缝里往下滴水,院口就能听见潺潺声,我娘说,这样建,冬不冷夏不闷,靠山吃山的道理全在屋檐上了。
这个宽阔的片子里,最显眼的是青砖灰瓦的大宅子,墙外就是成块的水田,秧苗碧绿发亮,风一吹像梳过的头发,小时候放学从田埂跑回家,脚面总被秧田的水花溅一身,回家挨唠叨,第二天照样蹚。
 这排石头门楼叫牌坊,忠孝节义一字排开,柱身上都是细密的缠枝和云纹,太阳斜过来,字迹被光一抹就活了,爷爷说,赶集路过要抬头看一眼,人活着总要有个准绳。
这排石头门楼叫牌坊,忠孝节义一字排开,柱身上都是细密的缠枝和云纹,太阳斜过来,字迹被光一抹就活了,爷爷说,赶集路过要抬头看一眼,人活着总要有个准绳。
 这堆鼓鼓的麻袋里是公粮,前头那位拿竹帚拨粮食,灰尘飞起来呛得人直眨眼,旁边小伙子脱了汗衫,往肩上一搭就成了凉披风,那时候交粮是正经事,家里大人一晚睡不实。
这堆鼓鼓的麻袋里是公粮,前头那位拿竹帚拨粮食,灰尘飞起来呛得人直眨眼,旁边小伙子脱了汗衫,往肩上一搭就成了凉披风,那时候交粮是正经事,家里大人一晚睡不实。
 这个木桶配木筛的家伙叫风车,把谷子倒进去,摇把子嗖嗖转,糠皮被风口吹出去,金灿灿的米粒就顺槽落下,我蹲在台阶上看半天,等大人不注意,抓一把谷子往空里抛,落地叮叮响。
这个木桶配木筛的家伙叫风车,把谷子倒进去,摇把子嗖嗖转,糠皮被风口吹出去,金灿灿的米粒就顺槽落下,我蹲在台阶上看半天,等大人不注意,抓一把谷子往空里抛,落地叮叮响。
 石坊底下围着的木桶是榨油桶的旧部件,孩子把它当凳子,男人把它当茶几,传说这里讲的是孝行,石硬话不硬,坐下歇口气也能听懂。
石坊底下围着的木桶是榨油桶的旧部件,孩子把它当凳子,男人把它当茶几,传说这里讲的是孝行,石硬话不硬,坐下歇口气也能听懂。
 这个气派的叫许国牌坊,八柱三间的格局,檐板雕龙刻凤,门洞里推着独轮车的人停下抬头看一眼,像是过门要行个礼,城里人说,从这儿进街,心里都要正一正。
这个气派的叫许国牌坊,八柱三间的格局,檐板雕龙刻凤,门洞里推着独轮车的人停下抬头看一眼,像是过门要行个礼,城里人说,从这儿进街,心里都要正一正。
 这位戴草帽的师傅,手里拿的是灰砖模样的坯料,旁边摆着木槌和刻刀,咔咔两下,边角就齐了,他说砖要起线,砌上墙才精神,现在机器一过,利索是利索,没了手味。
这位戴草帽的师傅,手里拿的是灰砖模样的坯料,旁边摆着木槌和刻刀,咔咔两下,边角就齐了,他说砖要起线,砌上墙才精神,现在机器一过,利索是利索,没了手味。
 这两位摆的一个是笤帚,一个是种子,竹把子上绑着高粱穗,拍到地上沙沙响,我娘买笤帚一定挑绑得紧的,回去扫院子,一下能把细灰都卷起。
这两位摆的一个是笤帚,一个是种子,竹把子上绑着高粱穗,拍到地上沙沙响,我娘买笤帚一定挑绑得紧的,回去扫院子,一下能把细灰都卷起。
 这个孤立在树影里的叫义坊,看着清冷,其实最热闹的是农忙时,挑担来往的人把扁担一横往柱脚一靠,喘口气再上路,石头被肩膀磨的地方微微发亮。
这个孤立在树影里的叫义坊,看着清冷,其实最热闹的是农忙时,挑担来往的人把扁担一横往柱脚一靠,喘口气再上路,石头被肩膀磨的地方微微发亮。
 这座有三重檐的小亭叫沙堤亭,檐角挑得很尖,亭下石板路直通村里,老辈人说,下雨天从这儿过,雨脚被檐口挡一挡,衣襟能少湿半截。
这座有三重檐的小亭叫沙堤亭,檐角挑得很尖,亭下石板路直通村里,老辈人说,下雨天从这儿过,雨脚被檐口挡一挡,衣襟能少湿半截。
 这条紧贴坡面的石阶直直插上去,台阶旁木棚里放着竹篾簸箕和柴草,白墙上的门楣花样繁复,傍晚鸡鸭就沿着台阶自己回窝,谁家晚了,院里一阵唤鸭声。
这条紧贴坡面的石阶直直插上去,台阶旁木棚里放着竹篾簸箕和柴草,白墙上的门楣花样繁复,傍晚鸡鸭就沿着台阶自己回窝,谁家晚了,院里一阵唤鸭声。
 这个黑黢黢的堂屋中央是天井,仰头一块天,雨从正中落下,石槽里积水亮得像镜子,奶奶说,有堂皆井是徽州人的讲究,采光排水全靠它。
这个黑黢黢的堂屋中央是天井,仰头一块天,雨从正中落下,石槽里积水亮得像镜子,奶奶说,有堂皆井是徽州人的讲究,采光排水全靠它。
 这座木屋搭在桥上,叫廊桥,下边是石墩,上头能纳凉,夏天割完稻,大家把镰刀栓在柱子上,坐着喝口茶,河风一吹,汗味就淡了。
这座木屋搭在桥上,叫廊桥,下边是石墩,上头能纳凉,夏天割完稻,大家把镰刀栓在柱子上,坐着喝口茶,河风一吹,汗味就淡了。
 这幅里最醒目的是水牛和长鞭,人扶着犁把,牛耳朵一抖,泥水就扒拉到腿上,我爸说,牛走直了,苗就排得齐,收割省事。
这幅里最醒目的是水牛和长鞭,人扶着犁把,牛耳朵一抖,泥水就扒拉到腿上,我爸说,牛走直了,苗就排得齐,收割省事。
 这排木柱子撑着的堂口叫宝纶阁,梁枋上黑漆剥落,露出木纹,柱间石栏杆刻着花草,站在台阶上说话,回声能从屋脊那里滚一圈再落下来。
这排木柱子撑着的堂口叫宝纶阁,梁枋上黑漆剥落,露出木纹,柱间石栏杆刻着花草,站在台阶上说话,回声能从屋脊那里滚一圈再落下来。
 这车子叫独轮大车,两边把手往上一抬,肩膀就和车成一条线,人把劲往前一拽,车轮吱呀吱呀转,路边稻把子像一堆堆小塔,走过一趟,汗水顺背脊直接滴到鞋里。
这车子叫独轮大车,两边把手往上一抬,肩膀就和车成一条线,人把劲往前一拽,车轮吱呀吱呀转,路边稻把子像一堆堆小塔,走过一趟,汗水顺背脊直接滴到鞋里。
 这条巷子外墙斑驳,马头墙像波浪一样起伏,红背心的小孩赶着一串鸭子,脚下啪嗒啪嗒,鸭子冲水沟里看两眼又被赶回来,笑声在墙缝间跑得飞快。
这条巷子外墙斑驳,马头墙像波浪一样起伏,红背心的小孩赶着一串鸭子,脚下啪嗒啪嗒,鸭子冲水沟里看两眼又被赶回来,笑声在墙缝间跑得飞快。
 这座七层八角的叫下尖塔,塔檐间长着灌木,像给老塔披了件绿袄,远看稳稳的,近看有点斑驳,老人说,这塔护村口风水,走夜路看见它,心就定了。
这座七层八角的叫下尖塔,塔檐间长着灌木,像给老塔披了件绿袄,远看稳稳的,近看有点斑驳,老人说,这塔护村口风水,走夜路看见它,心就定了。
 江上这些小船多是竹排和篷船,篷子用油布打过,雨点落上去噼啪直响,岸边屋舍排得密密的,晚饭时烟一起,水面就像蒙了层纱。
江上这些小船多是竹排和篷船,篷子用油布打过,雨点落上去噼啪直响,岸边屋舍排得密密的,晚饭时烟一起,水面就像蒙了层纱。
 这条街上,自行车铃叮当,板车吱呀,卖菜的把长豆角扛在肩上,一溜往前走,我在巷口买根冰棍,棍子木屑味重,甜在舌尖上,凉在后脖颈。
这条街上,自行车铃叮当,板车吱呀,卖菜的把长豆角扛在肩上,一溜往前走,我在巷口买根冰棍,棍子木屑味重,甜在舌尖上,凉在后脖颈。
 这扇高到顶的门叫雕花隔扇,开合时像风吹过竹林,墙角摆着酱缸铁锅,阿婆一边挪竹椅一边叮嘱,别靠着门,雕花容易掉刺。
这扇高到顶的门叫雕花隔扇,开合时像风吹过竹林,墙角摆着酱缸铁锅,阿婆一边挪竹椅一边叮嘱,别靠着门,雕花容易掉刺。
 这一对戴斗笠的母子,身后推的是水缸车,雨天巷子湿漉漉,石板泛着青光,小孩伸手摸斗笠沿,说娘你这帽檐能挡住一场大雨吗,娘笑着说,够咱走回家就行。
这一对戴斗笠的母子,身后推的是水缸车,雨天巷子湿漉漉,石板泛着青光,小孩伸手摸斗笠沿,说娘你这帽檐能挡住一场大雨吗,娘笑着说,够咱走回家就行。
 这张拍的是大户院子的天井,孩子们趴着门槛往里看,屋里摆着木桶扫帚,还有一口大木臼,听老人讲,敲年糕的时候,臼声能把一条街叫醒。
这张拍的是大户院子的天井,孩子们趴着门槛往里看,屋里摆着木桶扫帚,还有一口大木臼,听老人讲,敲年糕的时候,臼声能把一条街叫醒。
 这个摆在街口的叫小人书摊,木板上斜插着一本一本的连环画,封面色彩鲜得很,两个小孩一坐一站,翻得满手油印味,我那会儿最爱看**《三毛流浪记》**,一看就是半天。
这个摆在街口的叫小人书摊,木板上斜插着一本一本的连环画,封面色彩鲜得很,两个小孩一坐一站,翻得满手油印味,我那会儿最爱看**《三毛流浪记》**,一看就是半天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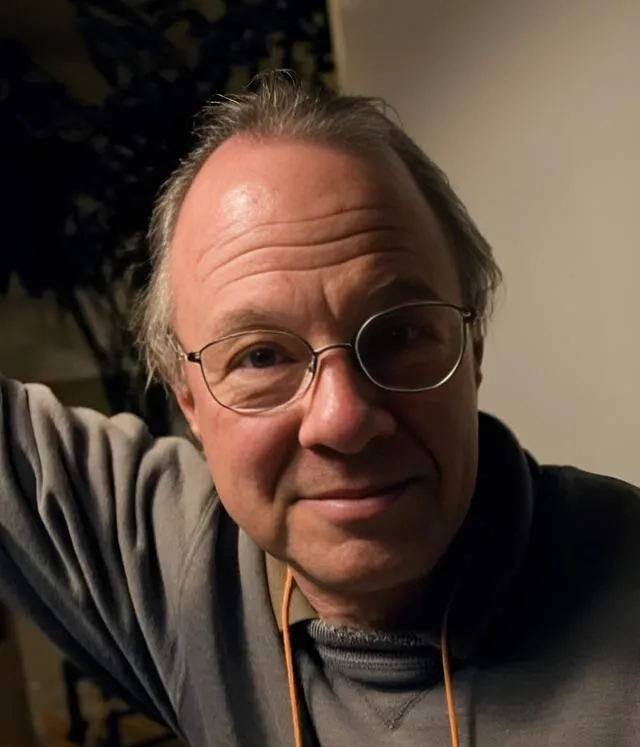 这位举着相机的外国朋友,把这一切都留住了,镜头里的人家、路、树和风,隔了这么多年再看,还是那股子古朴又自然,以前叫徽州,现在叫黄山市,名字换了,日子里的烟火气没散,山水也还是那山水。
这位举着相机的外国朋友,把这一切都留住了,镜头里的人家、路、树和风,隔了这么多年再看,还是那股子古朴又自然,以前叫徽州,现在叫黄山市,名字换了,日子里的烟火气没散,山水也还是那山水。